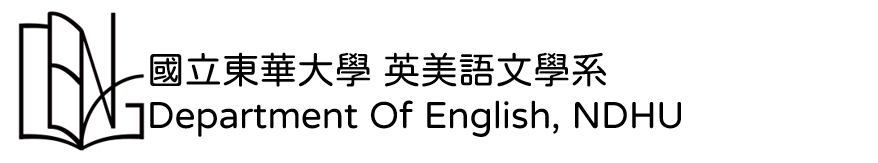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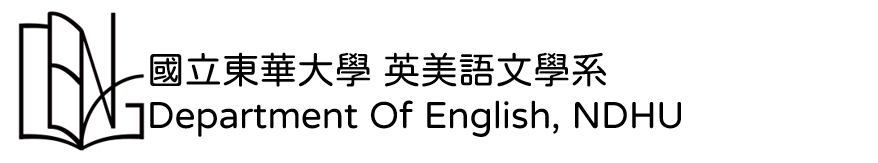
只要我願意,還是可以躲進去。
選擇就讀東華大學的原因?我的官方說法如下:「因為東華是新的學校。」
我喜歡新的課桌椅,我喜歡新的建築物,我喜歡新的宿舍,我喜歡一切都不曾沾染他人痕跡、還有很多空間可以發揮的感覺。事實上也沒錯。
不過,真正推動遷徙的原因,是花蓮遠離桃園,我可以得到更多自由。
後來,我得到推甄英美系的資格。面試前一天,我和母親搭火車來到花蓮,哇,山好大一片,我們都被窗外的風景給震撼到。花蓮的一切都很陌生,晚餐在旅館叫了買大送大的Pizza,兩個人吃到撐,有一種畢業旅行的感覺。隔天口試,我跟扮黑臉的系主任吳潛誠竟吵起了架,內容是關於《鐵達尼號》到底是不是爛片。還記得走出辦公室那一刻,與在外頭等待的母親對上了眼神,她熱切期盼點頭,我灰心喪志搖頭,當下只覺沒希望囉。離開花蓮之前,我們在市區吃了花蓮香扁食,彼此不發一語,當時若有對氣場敏感的人可能會看見我渾身發散出混濁的黑色毛邊吧。
不料,還是考上了。開學前,老爸租了計程車,把我所有家當都塞了進去,要送我去宿舍。那趟車程好遠好遠。看著窗外的風景,那一片無止無盡的山與海,我才隱約領悟這一切與我所想像的完全不同。
來了花蓮才知道,原本在西部生活中習以為常的物事在花蓮不一定存在。
原本對東華大學的嚮往,或許建立在嶄新的建築物上面──啊,我把對城市生活的期望投射進來了。在校園散步,總覺得天空與山脈未免離得太近。騎摩托車出門,有時還會被路邊茂盛而低垂的樹枝打臉,嘴巴如果張開開,甚至會吃到無數小飛蟲──雖然常和朋友抱怨,但蟲子誤闖嘴巴的時候我還是會呸呸呸地大笑,然後乖乖壓低安全帽的面罩。
身邊有些同學抱怨東華與世隔絕,說看不到什麼文藝演出,說沒有什麼東西好吃,一切都好無聊。於是他們週末經常回家,可能是臺北,可能是高雄。但我隻身一人享受著絕對的自由,不想常常回家,更愛上這種隨便一找都是祕密基地的簡單快樂。
難過時想要躲起來,緊張時想要躲起來,親密時想要和人一起躲起來,有太多地方可以藏,不管是早已封閉消失的保齡球館、行政大樓頂樓的平臺、幾乎沒有光害的操場長椅,或是能看見山脈與白雲的戶外游泳池,還是每逢節慶會特別點亮、被笑稱是巨大補蚊燈──裡頭充滿鴿子窩、鴿子便、飛蟲與讓人渾身發癢的奇怪灰塵的──理工大樓的燈樓,都讓那些青春狂放的夜晚不曾無聊。
任何人想過可以待的地方,我在東華的八年之間,幾乎都躲進去過。
那時還沒有智慧型手機(我當時手裡拿著的是暱稱「小海豚」的MOTOROLA CD928,當時可是全世界第一臺可以「中文輸入」的手機),廣闊的校地也不是什麼地方都有路燈,入夜之後就是濃度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黑。一開始擔心有蛇有小鳥,等蟲子吃多反而覺得無所謂了。就算起初懷抱著探險的心情,一旦躲進去某個空間,我就坐著賴著,偶爾躺在地板上。我未必知道想做什麼,只是亂想,想像未來會變成厲害的人,但那形象太遙遠,便不自覺反芻人際關係的苦惱或是深埋內心的各種祕密。那時,當我雙手抱膝藏身黑暗之中,彷彿聽見某個聲音說:「沒關係,你就做自己。」現在回頭看那些煩惱,實在好遠好小,甚至覺得是庸人自擾,但若不是當時有地方躲,我現在可能還在卡關。
從小生活在工業城市,就算眼前有一些近似自然的環境,也總在通勤上下學之間,在偶然的回望中驚覺:唉呀,兒時抓蟲子、打彈珠的廢田,其實土壤下埋了好多廢棄物;曾經以為的小河,其實是腐爛發臭的大水溝,我甚至見過水中漂浮著腐爛的水果與一頭豬屍。就算高中時終於讀到虎頭山旁的桃園高中,也因為課業的壓力不曾真正靠近自然,頂多在軍訓課烤肉時和同學們一起在山腰上的烤肉區玩耍。
「沒事不要進去虎頭山喔!」身邊好多人這樣說,不忘補充那裡很陰,山路深處發生過棄屍案……。這些耳語變成某種符咒,隱隱阻擋了我這一輩人想要隨時前往這座城市郊外小山的念頭。讀高中最接近大自然的時刻,可能是晚上留在桃園高中圖書館K書,坐膩了,便和一群同學在夜空下繞操場走,仰看滿天星斗,或是白天國文課在操場上方的大榕樹下聽課,享受微風。
雖然不上山沒有損失,在城市邊角也總有樂子,但每每在影視畫面看見類似《大河戀》海報那類小小的人被廣闊的綠色景觀包圍的構圖,內心總會生出一股淡淡的剝奪感。雖然不致對人生產生負面影響,但總覺得少了什麼,彷彿收集好久的集點卡始終缺了一兩枚貼紙。
留在花蓮的那八年(四年大學,一年教學實習,還有三年研究所),東華大學變成了我的祕密基地。可惜那時我不懂珍惜。畢竟活在這裡只要張開眼睛就是看見山、看見雲,當一切如此理所當然,自然也不會想到對未來的自己而言,今昔對照將是何等的殘酷。
畢業多年之後,我回到東華向學弟妹分享出版工作的經歷,這些臉上沒有皺紋的大學生,文靜地看著我,偶爾笑出聲音。我維持專業演講者的形象,對他們投擲精準計算過的笑話與出版知識──他們不會知道,剛才在計程車上,當我盯著校園內那些新冒出來的建築物,比對當年記憶,覺得好陌生,甚至有些慌亂;就連此時此刻我所身處的講堂以及剛才經過時偷瞥幾眼的教室,裡頭的課桌椅都已不再是全新的,上頭有鉛筆刻痕與原子筆墨水漬,牆壁也留下些許灰黑色痕跡與幾枚指紋,這一切都讓我心潮澎湃。
但窗外還有山,山上還有雲。「回桃園之後這些年,我不曾像這樣被山和雲包圍了。」
演講結束,我一個人在校園內散步,在文學院繞了繞,在最習慣的那一間廁所解手。我盯著熟悉的牆面,暗自計算上一次在這邊尿尿是多少年前的事。後來,我想起什麼,走到了文D104,教室裡頭有幾個學生正要從後門離開,我避開他們,躡手躡腳從前門走了進去,「以前的西洋文學概論、英國文學史、美國文學史,我是坐在哪一個位子呢?當初站在講臺上的老師們,現在又在哪裡呢?」
依稀記得大一的西洋文學概論課是早上十點開始,我經常睡過頭,梳洗後悠哉悠哉從擷雲莊去到文學院。當我和同伴站在教室後門邊,還很年輕的曾珍珍老師瞥見了,不多說什麼,頂多眼神示意:「沒關係,下一次不要遲到了。」
那個時候,我們都還很年輕啊。
現在,我已是大一新生父親的年紀了。
曾幾何時,買早餐不會有老闆叫我弟弟,在路上遇到強迫推銷沒有人喊我同學,在工作相關的場合都被尊稱一聲哥。二十多年過去,當初夜唱完還能騎車回學校上早八的我,如今去KTV對新歌排行榜已然陌生。沒想到在工作上走過某些榮耀時刻,以為已變得很強很偉大,越來越擅長虛張聲勢的自己,一旦踏上花蓮的土地,在山與雲之前,就變回當初小小的模樣。
不是降級,而是理解了的釋懷──變成大人的我,還是有地方可以藏。
無論我在外頭過得如何,有沒有長成當年期盼的模樣,曾經躲藏在這裡的時光都是真真切切的。現在的我學會與自己相處,透過漫長、安靜的等待,試圖觸碰、捉摸當時無法用文字述說的狂喜、鬱悶或卡卡的感受。我也不是孤零零地活著。曾經敞開雙臂讓我躲藏的祕密基地,曾經走進我的生命如今卻逐漸遙遠、甚至已經登出人生遊戲的老師與朋友們,就算物理性質上有所改變,但他們沒有消失,仍舊在這裡,在靜謐的黑暗或是無邊的山與雲之中。
只要我願意,還是可以躲進去。
文章出自:陳夏民 (2025)。〈只要我願意,還是可以躲進去〉。《迷信的無神論者》,頁29-40。桃園:逗點文創結社。